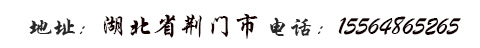家事梁建*思念父亲
|
父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父亲住在临双塔寺街的楼房里,晚年时,每当我看望父母离去时,父亲总是站在家中凉台上,望着我,直至我走远消失。如今父亲在凉台上的身影经常显现在我的脑海,且日益清晰。 父亲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爷爷没有文化,但还是想让父亲有些文化,送他读私塾。读完初小(小学四年级),为了生计,父亲来太原盛源昌货栈当小伙计,学徒做买卖。做学徒没有工钱,逢年过节也不能回家探亲,起早贪黑,扫院打水、侍奉掌柜,都是基本功。父亲非常勤勉,一有功夫就识字、学习珠算、记账,不懂就向师兄、掌柜求教。解放后,公私合营,几经辗转,他在东岗粮库做了一名会计,独当一面,不负所学。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故事。那时,一家6口人就挤在一张通铺上,小哥几个总是打打闹闹,难以入睡,父亲就给我们讲故事,条件就是,听完故事要睡觉。父亲就给我们讲《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岳飞传》的片段及一些戏曲《打金枝》、《鞭打芦花》等,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一些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及岳飞刻苦学习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岳飞自幼家境贫寒,发奋好学,没钱买笔墨,就在沙盘上练字学习,终成国家栋梁。看似不经意的故事,那些正义忠厚、勤奋好学、宽容善良的形象深深的烙在我们心里。 父亲非常勤劳节俭,节假日常常就是劳动节。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在压缩城镇人口时,户口回了农村,那时没户口就没工作,我们弟兄四人陆续出生上学,姐姐也在农村上学,老家的爷爷奶奶也要接济,就凭父亲一月四五十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父亲生性开朗乐观,从不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公休日就成了“劳动日”,到观家峪煤矿拣拾石头碳(煤矸石)、拉烧土、捋苍耳子换油等,以减少家里开支。煤矸石是煤矿上倒掉的没使用价值的黑石块,我们就挑那些比较轻的、夹着煤的,回来还能烧火,只是火旺时再放,否则就难以引燃,烧着后家里也特别呛, 的优点是免费。 开始时,父亲拉一个平车,清晨早早就出发了,中午吃些带来的饼子、开水充饥,直到下午才装满一车。一车煤矸石来斤,父亲拉,我们帮着推。后来,我十四五岁时,就父亲拉一辆车,我和二弟拉一辆车,算是给父亲减轻些负担。车一定要装匀,否则,那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的路就特别费劲。那时打煤糕,盖房子都是父亲当大工,我们当小工。 父亲特别重视我们文化课的学习。在那“读书无用”盛行的年月,在老家的姐姐来信,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父亲非常高兴,马上写信鼓励,并从微薄的工资中,每月给姐姐寄出生活费,供她住校学习。年,我初中毕业时,找工作是当时的潮流。我们一个年级5个班,报名上高中的仅有十四五人,我想找工作改善家里生活窘境,但父亲坚决鼓励我继续读高中。我们姐弟5人,有4人读了高中,在当时是不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太原市粮食系统开办电大班,我们在粮食系统的弟兄3人先后都考上了电大,在粮食系统绝无仅有,传为佳话。 父亲为人坦诚,工作勤奋,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业务,成为一名称职的会计师,在粮食系统小有名气。退休后,由于他的敬业和工作能力,单位领导换了几任,返聘留用他十几年。 现在,每当我路过父亲的老房子时,就会情不自禁的望向那个凉台、那扇窗户,房屋依旧,物是人非,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亲爱的父亲,我们想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usanqiq.com/cezcf/5616.html
- 上一篇文章: 传世偏方鼻炎
- 下一篇文章: 民间秘方专治牙痛的神奇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