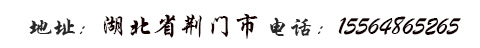曾国藩ldquo艺通于道rdquo
|
治白癜风自愈方法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130626/4197040.html中国最专业的书画艺术品收藏学习、交流、交易平台,满足普通大众“亲近艺术、感悟生活”的文化空间!集书画交流、研讨、鉴赏、养生、文论于一体,旨在弘扬我国 传统书画艺术,宣传高端书画人才,打造优质的书画艺术交流平台。 高震/文 内容提要:曾国藩“艺通于道”的书学主张,体现了其重视心性道德修养的书学思想。“艺通于道”即依艺体道、借艺明道;而书之“艺”指书法的师承取法、点画用笔、结体成势及刚柔风格等。他对书“道”的追求不限于“书品即人品”层面,最终旨在实现某种理想人格、精神境界乃至圣贤气象。道为“体”,艺为“用”,在习书实践中二者呈两进关系,皆须长期坚持方可臻于理想境界。 关键词:曾国藩书道书艺道与艺 儒家有“游于艺”的传统,故对“艺”与“道”的理解代不乏人,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写字即写“志”:“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①就书学之“道”、“艺”关系而言,曾国藩“艺通于道”主张的提出要早于刘熙载,他结合自身书法实践并借助日记书信,对“艺道一也”加以阐释,以为艺通于道即依艺体道,主张借艺明道,最终实现据艺进德。在他看来,书之“道”不能限于“书如其人”层面,而应超越“书品即人品”,实现某种理想人格、精神境界乃至圣贤气象。道为“体”,艺为“用”,书之“艺”表现在师法、用笔、结体及风格诸方面。曾国藩强调“艺道一也”,指二者在书法实践中须有恒方可臻于理想境界,故书道与书艺呈“两进”关系。 一 清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充国史馆协修官,在京期间叨陪从游于理学家唐鉴,醉心心性之学,而且以程朱为依归。与此同时,他和戴熙、顾莼、何绍基、钱振伦等书画名士过从甚密。与诸前辈同年的谈艺论文,对曾国藩“艺通于道”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意义。 就“艺”之层面言,书法家何绍基对曾国藩影响尤著。何、曾俱为湘籍,何虽较曾年长十二岁,但二人修身治艺颇多默契。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书中言:“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②,“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③。道咸以来,大书画家中祁寯藻、何绍基等人皆喜言宋诗,倡导为人为文皆应不俗;在与曾国藩论字研诗时,何绍基“人与文一”的诗学观自然作用于曾氏“艺通于道”的文艺观生成。曾国藩《赠何子贞前辈》诗云: 终年磨墨眼不眯,终日握管意未平。自言简笺通性道,要令天地佐平成。④此作当不晚于道光二十二年夏,“简笺通性道”非独何氏自白,亦为曾氏所认同。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曾氏日记中写道:“更初,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①因与何绍基谈诗论字得其要旨,而悟艺道相通之理。曾国藩的书学观、文艺观就此奠定。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致温弟沅弟》中说:“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论虽太高,然不能不为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则心有定向。”②在曾氏看来,诗文书画均属艺的范畴,而体道修身百虑一致,皆可经“游于艺”的方式以殊途同归。“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③书品与人品相通,“道”乃自身的道德修养,艺通于道即依艺体道,借艺明道,最终实现据艺进德。 曾国藩书法实践及书学理论,实属与理学相表里的心性修养之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临池不辍,即使带兵征伐、癣疾折磨亦不释笔,每日临帖之事必载于日记。若仅视其为对书法的痴迷,未免失之表面。借艺明性、据艺进德的书法体悟过程乃曾氏对崇高精神境界和圣贤气象的自觉追求,他说: 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④ 写字需要一种用志不分而凝于神的心理状态,习字过程其实也是修心养气的过程。书法体验作用于心性修养,心性修养又映射于书法实践,二者成双向作用。“申刻思作字之法,绵绵如蚕之吐丝,穆穆如玉之成璧。”⑤在曾国藩看来,“艺”之精全在于微妙处致力,作字做人皆须如此,绝不可心存浮名而作“乡愿字”。他将习字临帖系以心性修养一以贯之,并以此劝诫家人,其《谕纪泽纪鸿》云:“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元[玄]秘塔》,以药其病。”⑥必须明白,写字不能太随意任性,而应入门须正,立意须高。 曾国藩将其自身对立德、事功等的理解联系书论予以阐发。相较各种字体,他认为行书易于表现书者胸中的跌宕俊伟之气,他说:“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存丝毫求知见好之心则真气渫泄,无足观矣。不特技艺为然,即道德、事功,亦须将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⑦又谓:“是日因写手卷,思东坡‘守骏莫如跛’五字,凡技皆当知之。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时。余之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⑧由书法实践而悟及诗理,进而涉及为人持身之道,倘若没有平日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是不能就此悟入的。 二 由书法实践而体悟心性的过程也是格物,就此而言,曾氏对书之“艺通于道”的阐述践行已超越“书品即人品”这一层面,更多的是实现某种精神境界与圣贤气象。欧阳兆熊《水窗春呓》言曾国藩治学“一生凡三变”,于书法则“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①。欧阳兆熊关于曾氏书法早、中、晚年取法对象不同的表述大致不差,但系以三变却未免失之笼统;尤其曾国藩中年学*山谷之说,实属以偏概全。 受康熙、乾隆二帝的影响,清廷流行董其昌和赵孟頫的书法。道光十九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写唐诩庭寿屏,福青缎写*字,字学柳诚悬,参以王大令、董香光笔意,结构甚紧,笔下飒爽雅健,甚自许也。”②董其昌书法宗米芾,且取唐柳公权行书之疏淡而自成一家。此时曾国藩字学柳公权,并参以晋王献之、明董其昌笔意,以“飒爽雅健”自许,不难见其旨趣。后来曾国藩不独取法柳体,在间架上亦师法赵孟頫,他说: 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③ 曾国藩虽以四十岁后书法略有长进,但“时慕欧、柳,时慕赵、董,趋向无定,作辍靡常”④。“余年已五十,而作书无一定之风格,屡有迁变,殊为可愧。”⑤因认识到趋无定向而致缺乏一定之风格,曾国藩中年后特专心师法李邕《岳麓寺碑》,历时八年而终有进境。他以为:“大约书法不外羲、献父子。余以师羲不可遽几,则先师欧阳信本;师欧阳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不可遽几,则先师虞永兴;师虞不可遽几,则先师*山谷。二路并进,必有合处。”⑥“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而辅之以李北海;丰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山谷。”⑦“二路并进”指分别师法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两路。 具体来说,曾国藩以王羲之、欧阳询、李邕的“间架”为一路;王献之、虞世南、*庭坚的“丰神”为一路,于间架师法欧、李,于丰神则资虞、*。他在晚年尤强调专法某家的必要:“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定以后楷书学虞、刘、李、王,取横势,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书学欧、张、*、郑,取直势,以尽睨视之态,利在稍瘦。二者兼营并进,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⑧同治六年,年近六十的曾氏作一联曰:“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潮、程春海;二祖谓羲、献,六宗谓欧、虞、褚、李、柳、*也。”⑨犹奉虞、李、欧、*为宗,并参以本朝刘墉、李春潮、程恩泽三家,博观而约取,不失为晚年自道书学依归之言。他认为: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①用笔循道,结字有法,点画用笔与结体成势乃书法的基本要领,曾氏一生于此两端之体认甚为着力。点画用笔不离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八字,曾国藩对八法的体悟,确如其谕子之言,即多观古人墨迹。譬如关于“磔法”,他说:“如右手掷石以投人,若向左边平掷则不得势,若向右边往上掷,则与捺末之磔相似,横末之磔亦犹是也。”②这是就横笔磔法言。关于努笔,他认为:“用笔贵勒贵努,而不可过露勒努之迹;精心运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于用勒用努者。”③再如谈偃笔、抽笔:“日内作书,思偃笔多用之于横,抽笔多用之于竖。竖法宜努、抽并用,横法宜勒、偃并用。”④与抽、偃不同,曾国藩认为竖笔用努、勒更易体现俊拔之气,因此也将其与“直”、“觩”同列为书体“阳德之美”四端。 用笔之道不离用锋,曾国藩说:“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蹲锋。”⑤可知蹲锋缘于偏锋。他“阅刘石庵《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张得天之起笔,多师褚、颜两家,用直来横受之法,故不藏锋”⑥。但曾氏以为藏锋与否,只是运笔行迹之别,无碍字体机趣的发挥。点画用锋之外,曾国藩在具体书法实践中于执笔运腕之法亦多心得,他说: 因用狼笔写新宣纸,悟古人顿挫之法、扑笔之法,只是笔不入纸,使劲扑下耳。⑦ 与“笔不入纸”相系,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得好字出;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⑧执笔运腕表面上是手和笔的关系,实为笔与纸的关系,《致温弟沅弟》言换笔之法:“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笔用。……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中常觉其方。”⑨因心有方向故能下笔四面有锋,此已上升为笔与心的关系了。 结字大体有法,但笔法变化无穷,曾国藩于此特别强调“但求胸有成竹耳”;而落笔结体要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⑩由单字笔画之点到结构之体,再至数字数行之势,故势乃体之基础上体现出的书法整体风格。“势”在古代不独见于书论,画论、音乐、兵法均讲势,而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更启后世以势论文之先河。由刘勰“即体成势”、“形生势成”、“势有刚柔”等阐述知“势”即文章的整体风格,乃由行文结构的安排而体现。曾国藩论书颇喜言“势”,且与刘勰以文章风格论势相通,他以为:“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①笔笔皆须有势,这就涉及“取势”问题,他说: 出笔宜颠腹互用,取势宜正斜并见。用笔之颠,则取正势,有破空而下之象;用笔之腹,则取斜势,有骩属翩跹之象。② 体无定法,故循体所成之势亦不 。借笔颠、笔腹分取正斜二势以成不同之象,“笔—势—象”,由彼生此,环环相扣;而书法的更高境界是笔的颠腹互用,如此方能因势成象,既可破空向下,又能翩跹回环。曾国藩书论还涉及“阵”、“节”,他说:“因悟作字之道,全以笔阵为主,若直以取势,横以出力,当少胜矣。”③又谓:“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④与势类似,阵、节亦系援兵法以论书法例,《孙膑兵法》有“八阵”、“十阵”、“势备”篇,而“鸷鸟”句出《孙子兵法·势篇》,鸷鸟因能“节量远近”,致其势险急而足以折物。曾国藩熟读兵书,故能于书论中融以兵法而愈显形象。 三 曾国藩于古文之道尤服膺姚氏,自述:“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⑤姚鼐论文分阳刚与阴柔两大类,曾国藩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⑥缘于“易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的哲学思想,不独作用于曾国藩的文学观,亦深刻影响到其书学观。 阴阳为立天之道,刚柔乃立地之道,相对于“刚正在内”的坎卦,“离之为卦,以柔为正”⑦,故以阳刚阴柔论文虽分二端,于《易》则系乾、坤、坎、离四卦。早在道光年间,曾国藩与何绍基讲字时提出:“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⑧曾国藩引易理论书法实肇于此。他此时以乾坤二卦论书,是将书法的风格与结构对举,稍异于日后以阳刚、阴柔二端纯就风格或间架论书。由阴阳刚柔演绎发挥的系列书学观点,咸丰以后多见于曾国藩书论之中,如: (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⑨ 二磺隆是由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研制开发的 合成酶抑制类除草剂,杂草通过根和叶吸收后,在植株体内传导,使杂草停止生长后枯死,其具有残效期短、广谱、高效、无残留药害、对环境友好等优点[11]。双氟磺草胺是由美国陶氏农业科学公司开发的三唑并嘧啶磺 类除草剂,是一种典型的 合成酶抑制剂[12]。该药剂为苗后茎叶处理的广谱除草剂,主要用于防除小麦田阔叶杂草,其施药期长,冬前至早春均可,且适宜与其他除草剂、杀菌剂、植调剂等混用[13]。为了明确1% 二磺隆·双氟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对小麦田杂草的防除效果、使用剂量及对小麦的安全性,进行相关的田间药效试验。 援《易》以入书法,由早年提出的乾道、坤道,到咸丰间雄奇、淡远,再至同治时阳德之美、阴德之美,两两对举复一脉相承。曾国藩同治三年说:“写零字甚多。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二者阙一不可,亦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②同治三年以前,曾国藩论结构主张八端兼备,论风格力求合雄奇于淡远,或刚健参以婀娜,或险劲兼之自然,如此方为成体之书。 就书法实践言,结构可以八体兼备,但风格很难做到诸貌共呈,何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曾国藩同治四年十月的日记正体现出这一认识上的转变:“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营并骛,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③书法于阳刚、阴柔之美须意存一端,心若有旁骛则笔意两失。然曾国藩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其日记书信中相关书论亦多着力阳刚之美。咸丰十一年由董香光渴笔法而悟“余当以渴笔写吾雄直之气耳”④。同治元年读李、杜诗文,“悟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证果”⑤。惊心动魄处所代表的气势不独见之于书论,曾氏抄古文、选古近诗列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诸属,亦将气势置首,内中不无用意。 曾国藩书论每借书艺之阐述以体现书道内涵,显然道与艺呈体用关系。艺之为用,其最鲜明特征即含有“技”的色彩;因“技”皆遵循一定的成法,法与道有相通处,这也是艺能通道、艺能载道的原因。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日记载: 昨日,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工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⑥ 朱熹“鸡伏卵”乃因读书而发,强调旧学仍需“反转看”的温故知新之义,主旨不离一“熟”字。曾国藩于此颇为用心,咸丰九年四月初八习字,于日记中再次提到:“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梓匠之规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人有恒言,曰‘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⑦作字求熟不离一“恒”字,同时还要具备“识”,即所谓规模间架,理同朱熹之“猛火煮”。朱熹说:“今语学问,正如煮物相似,须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复自家元来之性,乃恁地悠悠,几时会做得?大要须先立头绪。头绪既立,然后有所持守。”⑧曾国藩深谙理学,且日常修身养气对朱子之言颇多体认,多借书论之阐发以体道言道,书艺也因此承载了道。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因见何绍基作字,称赞其学养兼到并认为“天下事皆须沉潜为之,乃有所成,道艺一也”①。艺道一也,即进艺、进道之理相同,皆须沉潜勤勉方可精进。道艺并进,离不开“勤”,曾国藩一生好学不倦,对碑帖之学情有所钟,于书艺书道的践行体悟都极好地诠释了勤。他在咸丰元年七月廿三日的日记里说: 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②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日记载: 日内作书,常有长进,盖以每日临摹不间断之故。③ 曾国藩认为作字之道,不多则不熟不速,今古名人无一例外。倘若将心性修养、精神境界的臻于至善及圣贤气象的最终养成视为进道之 目标,那么书艺之进最终追求的乃是具备一家之面貌神态。曾国藩晚年书论多注意到书法的神、韵、气,即书法之意境美。他以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④曾国藩在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说: 偶思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以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功夫。⑤ 相较于笔墨形态的形式美,意境蕴涵着书作的神态风韵,故对笔墨形态的用心最终乃为呈现出迥绝群伦的一种面貌神态。曾国藩说:“(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近来作书,略有长进,但少萧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风韵耳。”⑥对意态和萧然物外之致的追求,即为实现一种以风韵胜的书法境界。风韵之外,曾国藩亦强调书法的气势,以为:“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⑦曾国藩论书重“势”,“势”作为某种书法风格更有助于表现其所向往的阳刚之美,故“气势”也自然成为曾国藩书学的审美范畴。在他看来,书法作为“艺”之修炼在精神上与“道”相通,下学上达,精义入神,最终皆可臻至圣贤名家气象。 (原载于《文学与文化》年第3期) 转载声明:本文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 时间删除内容!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和收藏名家作品,中国书法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tusanqiq.com/cezjg/7766.html
- 上一篇文章: 北京传统村落,你知道几个
- 下一篇文章: 掌健识上海肾脏周肾病患者用药有禁忌